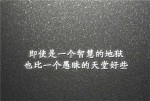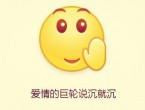村庄里的小溪的作文【一】
在经历了三十年多改革开放这样深刻变革的时代,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有过村庄的回忆。要离开村庄,如今并不困难,背上一个行囊,北上或南下,就能够迅速地让村庄成为你的思念。但是,离开村庄的你,还回得去吗?
也许,你的村庄消失在钢筋水泥的楼群里,你的老屋早已推倒,成为一座新城的一角。总之,你住过的村庄已然不在。或者也许,你的村庄非常幸运地、依然青山绿水地耸立着,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城市生活的梦还能嫁接得上那里的十里稻香吗?你还能追寻得到乡村少年的足迹吗?现在的村庄还是你住过的村庄吗?
读熊培云先生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总是让我发出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追问,关于村庄的追问。也许,是因为我也有过在村庄里生活成长的经历,也有过几乎逃离般地离开村庄的历程。有过这样的经验的,一定有许多许多人。就如熊培云先生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当农村源源不断地把生产资料送往城市的时候,城市的工业化得以提速,城市生活有了切实的保障,而农村却因资金贫乏、人才匮乏、政策限制,而呈现出一定的衰败和沦陷。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通过升学、入伍、进城打工的方式,离开他们的家园。这有什么办法呢?不离开,就意味着可能没有前途,没有更美好的生活。
作为千千万万离开村庄中的一员,我承认,二十多年前,当我离开村庄,踏上城市、跨进工厂门槛的那一瞬,是多么欣喜,值得庆幸。但随之而生的,是我对村庄的无限牵挂,因为那里还生活着我的父母。有时候,我倒是觉得,村庄已不是我的村庄,这不是我的错,因为,当我离开村庄的时候,我的田地就被其他村民“瓜分”了。只要户口从村里迁出,虽然是生于斯长于斯,但从法律意义上你已彻底不属于这个村庄了。城乡之间的楚河汉界就是如此分明。
造成这种诡异结局的原因,常常会直指那个阻碍城乡交流的户籍制度。好在,冰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到今天似乎有了消融的一天。社会的改良和变迁,并不像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那样立竿见影,总是在经历很长的努力后,才艰难地向前迈上一步。所以,我们对于村庄的期待,也不必那么悲观和失望。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在的村庄大多看不到古树,也不见了小桥流水、鸡鸭成群、牧童横笛。可是,没有这些就不是村庄了吗?对于这些心怀念想没有问题,谁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村庄。但是,究竟是谁,还想保留着这样原生态的农村?如果出于对农村乡土历史的研究,这情有可原;出于对乡村旅游前景的考虑,也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可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让早年逃离乡村的人——如今的新兴的城市人,满足他们的怀乡之心,就要让这样的村庄长久地保持着她的原始模样,那就显得过于矫情或者是自私了。因为,经历过原生态农村生活的人,都会苦恼于在农村谋生的不易、出行的艰难,还有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的糟糕。
谁人故乡不“沦陷”?也许真的是如此。但是,在“沦陷”的同时,是不是又有一种新生的力量在生长?当我的村庄被拆得只剩下几户人家的时候,我也并不想坚守。因为新农村的建设更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出行更加便利,生活更加舒适,父母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会更加健康长寿。当年过古稀的父母也领到了社保金,享受到农村医疗保险的种种好处,我深切地感受到,如今村庄的变化,已不仅仅只是她的外形,还有影响人的内心的东西也在滋长,村庄里的人也显得更加自信了。
所以,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熊培云先生对他所住的小堡村以及类似中国村庄的认识也在一步一步地深化。他是一个建设型的学者,他在叙述着对村庄的依恋,也在用他的力量,试图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村庄的面貌。他在他的小县城建起了一座图书馆,以实现他的“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因为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
我们是不是可以如熊培云先生那样,不管曾经以何种方式逃离村庄,今天都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去回馈你的村庄,让她更加富足、文明,自由而富于理性。只有这样,才可以打破人才、资源在农村只出不进的所谓“鱼笱效应”,通过反哺与回流,实现现代乡村的复兴。到那时,你住过的村庄还在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已经不重要了。
村庄里的小溪的作文【二】
熊培云说:“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可是,谁没有故乡呢?没有故乡的人还是人吗?沈从文后,葬在故乡凤凰,他的外甥黄永玉将他的这句话刻在墓碑上:一个士兵要不战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可以说,活着的人,都像孤魂野鬼一样四处奔波飘零,而去的人,才真正回到了天堂一般的故乡。
静心阅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行走在熊培云式温暖柔和、清明理性的语言缝隙,我时不时地想起我内心的村庄,我眼里的中国。有回忆,有对比,有感动,有沉重。为熊培云式提着笔杆子出了乡村又时时不忘回顾反哺的游子,也为我兄弟姐妹一样无数远离家乡四处打工觅食的民工,还为那些留守故园陪伴日升月落鸡鸣犬吠的老弱,更为滋养了我的童年我的悲喜我的理想的那一片山水——我的眼里时常涌起泪水,我的心头时常挂起一轮明月。
一
今年正月,回家过年。村里又是一番新变化。村口新修了宽敞的水泥路,安装了高高的路灯,就连各个小巷也铺了水泥。母亲说,村里正在忙着搞“三直”。所谓“三直”,就是将所有田地重新整合成一块块整齐划一的方格,中间开辟一条条笔直的机耕车道,以适应机械化耕作,即田埂直、沟渠直、道路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村里搞过的“园田规划”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也算是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那么,田野之间的一个个河塘呢?我着急地问。母亲说,也都推平了,不要了,只留下了后港没有动。我又问:大家的自留地呢?母亲说,自留地也都推平了,会重新分配。陡然间,我的`心情黯淡下来。那些池塘,可是我童年嬉戏的场所啊!车水、游泳,采莲、摘菱,捕鱼、挖藕……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他们还起着灌溉的大作用呢!母亲也说不出话,只是一声叹息。之后我和村干部聊起,他们说,灌溉的事不用担心,村里准备投资改造电排站,需要抗旱的话就从村前的大港(万年河取水。那万一大港也干得没有水呢?我的诘问,村干部答不上来,他们只强调是上边叫这么干的,是政府统一部署。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熊培云的诘问,直达问题的内核。假如农民是土地的所有权人,农民自然会知道怎么打理自己的地产,用得着并不真懂种田的官员们指手画脚吗?关于土地权属问题,其实最和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相连。“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而大部分中国人为什么还是可望不可即呢?眼下烽烟四起的腐败卖地、野蛮拆迁,就为这种国有民无的土地政策作了鲜明的注脚。征询村干部今年还有什么新规划,他们说正在申请县里立项,全面建造村里的自来水管网,使村里人都喝上自来水。我说,现在的村民喝水都是自己使用手动压水机,不要花钱的,如果换了自来水,费用可不能贵了,否则村民们不会要的。村干部说,也就收一块左右一个立方吧。对此,我只存疑。因为在走访外地的村庄时,我也见到过不少弃置不用的自来水管网,白白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试想,在有免费水喝的前提下,哪个村民希望多花钱呢?应该说,我家乡的村干部还是想干点实事的。他们对村里的卫生、休闲、文化等设施改造与重建,都有一些良好的愿景或规划。但怕就怕他们受了上级部门的瞎指挥,不征求村民的同意,干一些乡邻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是通过村民选举上来的,但这个选举更多的是掺了宗法宗族的势力,而且监督机制远不完备。目前,靠的还是个人的一点德行吧。但,只有德行,靠得住吗?
我的村庄比较大,有近两千人口,农田近两千亩,山林数千亩。面对如今盛行的卖地、卖山、卖树歪风,村干部一行把持得住吗?我心头不能不泛起“谁人故乡不沦陷”的忧思。
二
关于中国乡村,各人有各人的观照角度和愿望期许。
很多城市生、城市长的知识分子,研究三农、评判三农,更多的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持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记得在南京参加一个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论坛时,来自某县县委的一个干部说到村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很是落后、急需教育时,听讲的一个出自河南农村的学者愤而站起,当堂责问:你们干部的素质就比他们好吗?我看还不如他们!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说的也许都没错,只是各自的视角不同,观点就不同。但在情绪上,我还是赞同后者的观点。在当今中国,重要的不是教育人民,而是教育官员。就拿村委会选举来说,真正的民主应是自上而下的,哪有上面是专制的锅盖,而指望闷民主的熟饭呢?这样的熟饭不变味变馊才怪!这样的民主不被闷才怪!就像小沈阳说的,你忽悠人可以,但不带这样忽悠人的!
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觉得在对待三农问题上,国人最应该防范的几种心态是:
1.观光客心理。
国人拜改革开放所赐,腰包略微鼓了起来,于是旅游之风大兴。很多游客有这样的心理:希望看到更多原生态、原始状的风景,比如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边远山民的生活状态、乡村田园的自然样貌。走到一个地方,就希望有古老阴暗的民居,有破败不堪的古董,有曲里拐弯的小路,最好还要有衣着破旧的老人、辛苦劳作的农夫作为点缀。然后拍照、合影,吟诗、写游记。让他们留宿一两晚,则照片拍得更多,诗文写得更好。但若要他们从此留下来,做一个永住民,他们则是不干的。因为,受不了这里的清苦和闭塞,寂寞和冷清。那么将心比心,你需要舒适、富贵、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不需要和不向往吗?你认为要保留、挽留的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如果不是他们想保留、挽留的,你有什么好叹息好批评的呢?追求幸福,是每一个地球人的权利。在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无数村民也期待着革故鼎新,从此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享受国家正式公民的福利待遇,这有什么错呢?不能因为要照顾你的旅游你的拍摄你的写作,就让他们长期生活在看上去很美很诗意、实际上落后、清贫、辛劳的境遇中;也不能为了满足一部分文化人的所谓学术研究工作,而使另一部分人躲开现代化,仍旧生活在古代吧。
2.吊丧者心理。
几十年来,虽然城乡剪刀差依然严重,但乡村的巨大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纵向比,乡村的进步指数、乡民的幸福指数显然有大幅度增长,试问儿辈、孙辈的生活感受,是不是都远远地强过父辈、爷辈;横向比,和中国城里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些城市无产者的生活水准可能真的还不如农村,怪不得一些地方的农业户口比非农户口更受捧,一些有钱人也将房产投资的眼光落在乡村的土地上。当然,这一切变化,源于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兑现,源于广大青壮年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赚得一些汗钱,还由于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衍生了一系列居住、饮食、环境、交通等方面的恶劣问题,使得城市居民略有啧言。我就有亲身体会:每次回乡,都会捎带一些母亲、岳母亲自耕种的蔬菜;每次吃着家乡的饭食,都觉得余味不绝;看着亲邻们建造的宽大楼房,对比一下自己的套房,简直有蜗居之感。还有他们的悠闲,缓慢,也是我们上班一族颇为艳羡的。
但有一部分身居城市的人,眼光和思维总是停留在前几十年的光阴里,看到的总是残破的村庄、贫穷的村民,想到的总是无尽的哀伤、不绝的痛苦。我承认,农村的确还有残破、贫穷、哀伤、痛苦,但一定不是大面积的,不是主流的面貌,而他们往往喜欢选择性取材,用放大镜观察农村的弊病,用立体音响聆听农人的呻吟,于是常发吊丧之痛,常写哀鸣之字。这些人往往喜欢舞文弄墨,遐想行吟,过度继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情怀。
当然,中国的乡村远未达到我们理想的境地,比起英美日韩等国的乡村主义、乡村精神来,差距何止千万里。但我们不正在追赶吗?不正在建设吗?我们需要鼓舞,不需要吊丧;需要批评,不需要悲泣。
3.救世主心理。
中国人吃透了“救世主”的亏。远的不说,我们父辈眼里的救世主,就是那将天下打得一片红的东方红老人,他真的救了国人救了世人吗?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当有定论。
自从2000年湖北某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喊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心声后,三农问题就更加引发了朝野关注。的确,欲认识中国,必先认识中国的乡村;欲发展中国,必先发展中国的乡村。无他,只因中国是一大农业国也。无数有识之士都投入到认识中国乡村、发展中国乡村、拯救中国乡村的言论或行动中来。他们的心愿,或曰动机,不可谓不好,不可谓不高尚。著书、立说,捐款、捐物,建希望小学、做图书馆,宣传民主、发动选举……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能做的,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常常为之感动,为之眼湿。济弱扶倾,仁慈隐恻,人心向善,善莫大焉。但若据此高人一等,颐指气使,以为布施,居功自得,俨然一副救世主心理,那么这样的拯救不要也罢。
其实,乡村是有自救统的。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有着厚实的伦理根基,长期稳定有序,建设有加。是近现代史上的所谓革命,所谓主义,将它颠覆破坏,盘根推移,而今元气大伤,人心不古。
说到乡村的自救,我们很多城市居民当会脸红气短。今年春节前后,广东陆丰乌坎村反腐游行,理性抗争,争选举自由,保自家权利,可谓震惊中外。谁说农民见识浅陋,贪图小利?谁说农民卑微如草,素质低下?还有那些在圈地运动中长年上访,对侵权行为坚决说不的无数村民,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还称不上是英雄壮举吗?在这样一个羊恋上狼,狼欺负羊的时代,究竟谁更需要拯救?
乡村建设无须悲观。只要全能政府不再全能,撤出不必要的管理触须,还自由于民,假以时日,我们期许的乡土中国可复苏矣!
当然,这需要我们全体国人的努力,抗争。
三
熊培云把故乡比做灵魂的庙宇,有故乡的人当心存敬畏。我心有戚戚焉。
网上读到浙江陈国明先生所作的七律一首:
清宵作梦到山乡,野菊花开特地香。
半亩寒塘鱼跃水,三间暖屋竹齐墙。
村头犬吠新来客,宅畔人喧旧晒场。
一觉醒时天露白,倚床枯坐忆亲娘。
哪里有亲娘,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故乡啊,祖国!
村庄里的小溪的作文【三】
在经历了三十年多改革开放这样深刻变革的时代,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有过村庄的回忆。要离开村庄,如今并不困难,背上一个行囊,北上或南下,就能够迅速地让村庄成为你的思念。但是,离开村庄的你,还回得去吗?
也许,你的村庄消失在钢筋水泥的楼群里,你的老屋早已推倒,成为一座新城的一角。总之,你住过的村庄已然不在。或者也许,你的村庄非常幸运地、依然青山绿水地耸立着,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城市生活的梦还能嫁接得上那里的十里稻香吗?你还能追寻得到乡村少年的足迹吗?现在的村庄还是你住过的村庄吗?
读熊培云先生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总是让我发出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追问,关于村庄的追问。也许,是因为我也有过在村庄里生活成长的经历,也有过几乎逃离般地离开村庄的历程。有过这样的的,一定有许多许多人。
就如熊培云先生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当农村源源不断地把生产资料送往城市的时候,城市的工业化得以提速,城市生活有了切实的保障,而农村却因资金贫乏、人才匮乏、政策限制,而呈现出一定的衰败和沦陷。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通过升学、入伍、进城打工的方式,离开他们的家园。这有什么办法呢?不离开,就意味着可能没有前途,没有更美好的生活。
作为千千万万离开村庄中的一员,我承认,二十多年前,当我离开村庄,踏上城市、跨进工厂门槛的那一瞬,是多么欣喜,值得庆幸。但随之而生的,是我对村庄的无限牵挂,因为那里还生活着我的父母。有时候,我倒是觉得,村庄已不是我的村庄,这不是我的错,因为,当我离开村庄的时候,我的田地就被其他村民“瓜分”了。只要户口从村里迁出,虽然是生于斯长于斯,但从法律意义上你已彻底不属于这个村庄了。城乡之间的楚河汉界就是如此分明。
造成这种诡异结局的原因,常常会直指那个阻碍城乡交流的户籍制度。好在,冰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到今天似乎有了消融的一天。社会的改良和变迁,并不像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那样立竿见影,总是在经历很长的努力后,才艰难地向前迈上一步。所以,我们对于村庄的期待,也不必那么悲观和失望。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在的村庄大多看不到古树,也不见了小桥流水、鸡鸭成群、牧童横笛。可是,没有这些就不是村庄了吗?对于这些心怀念想没有问题,谁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村庄。但是,究竟是谁,还想保留着这样原生态的农村?如果出于对农村乡土历史的研究,这情有可原;出于对乡村旅游前景的考虑,也在可以理解的范畴。可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让早年逃离乡村的人——如今的新兴的城市人,满足他们的怀乡之心,就要让这样的村庄长久地保持着她的原始模样,那就显得过于矫情或者是自私了。因为,经历过原生态农村生活的人,都会苦恼于在农村谋生的不易、出行的艰难,还有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的糟糕。
谁人故乡不“沦陷”?也许真的是如此。但是,在“沦陷”的同时,是不是又有一种新生的力量在生长?当我的村庄被拆得只剩下几户人家的时候,我也并不想坚守。因为新农村的建设更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出行更加便利,生活更加舒适,父母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会更加健康长寿。当年过古稀的父母也领到了社保金,享受到农村医疗保险的种种好处,我深切地感受到,如今村庄的变化,已不仅仅只是她的外形,还有影响人的内心的东西也在滋长,村庄里的人也显得更加自信了。
所以,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熊培云先生对他所住的小堡村以及类似中国村庄的认识也在一步一步地深化。他是一个建设型的学者,他在叙述着对村庄的依恋,也在用他的力量,试图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村庄的面貌。他在他的小县城建起了一座图书馆,以实现他的“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因为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
我们是不是可以如熊培云先生那样,不管曾经以何种方式逃离村庄,今天都能够以自己的能力去回馈你的村庄,让她更加富足、文明,自由而富于理性。只有这样,才可以打破人才、资源在农村只出不进的所谓“鱼笱效应”,通过反哺与回流,实现现代乡村的复兴。到那时,你住过的村庄还在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