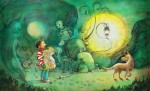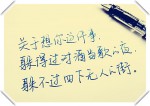芬芳了我的岁月作文【一】
啊,我的蛋糕!我猜想到蛋糕可能被偷,所以赶紧跑到房间。蛋糕,我的蛋糕,在短短的几分钟内“飘”走了,怎么会这样,难道我在做梦吗?不,事实告诉我,我的蛋糕的.的确确被偷了,而且,偷蛋糕的人还是一个神偷!他实在太厉害了,几分钟内偷走蛋糕,而且在我刚刚买回来,去洗手的几分钟内偷走。他怎么知道这个时候我有蛋糕呢?哼,一定是家贼!那么,会是谁呢?为了“飘”走的蛋糕,为了泡汤了的美味下午茶,为了咕咕叫的肚子,我决定抓出这个可恨的贼,讨回公道!
我想:蛋糕那么香,吃了的人身上肯定有一股香喷喷的朱古力味。好,就从这里查起!妈妈在楼下看书,我跑过去,闻了闻。呵,除了一股香水味,其他什么都闻不出。二妹在那里写作业,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就是那个贼。我走过去,从上闻到下,又从下闻到上。呸,除了一股臭汗味,什么味都没有了。妹妹问我:“你有病啊?今天怪怪的,到处闻人,怀疑你变态。”我当时正有火,便大声地喊:“好心你啦,身上臭得要,还不去冲凉!”接下来,目标就是――小妹!看她,左手捧着一盒饼干,右手拿着一个甜筒,嘴里还吃着薯片,看了不晕也要倒。唉,就他那个饿鬼的样,我想她也不会去偷蛋糕,吃了蛋糕难道还能吃下那么多零食吗?唉,烦啊,烦啊,到底是谁?是谁动了我的蛋糕?
芬芳了我的岁月作文【二】
秋天的公园里,我坐在长椅上,看红枫叶翩翩着飞舞着落下,那一片片枯黄的树叶如同一张张褪色的老照片,向我讲述一段段故事,我不禁浮想联翩。
那同样是一个红叶纷飞的秋天。9月,我认识了一个与我同名的女孩儿。我对她充满了兴趣。然而,也许这就是缘份吧,不久后我们做了同桌。
我渐渐发现了那个看似淑女可爱的她竟是个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女生。
“放学一起走吧!”我正低头忙着整理书包,一个甜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好啊!”我抬起头朝她笑了笑。
下课铃响起,我们挽起手,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校门。随后,转进一个安静的小路上,小路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松软的金黄落叶,不是有几片鲜红的叶子夹杂在其中,像是金黄沙滩上的红贝壳。
最初,我们似乎都有些羞涩,小路上安静的`可以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突然,她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畔,“你知道吗?我以前很喜欢把漂亮的叶子夹在玻璃板中,然后写上自己喜欢的一句话。”
我的热情瞬间就被她这神经质的行为感染了,“是吗?那该很有趣吧!”说着,我捡起两片落叶,小心地放在手掌上。“让我也试试”……我俩开始谈论女生之间的琐碎小事。不知不觉中,天渐渐暗了。
告别时,她对我说:“注意安全哦!天黑了,要走大路,拜拜!”她很细心,短短的一句话令我无比温暖。我过了马路,回头一看,她依旧站在原地,注视着我离开的方向。瞬间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夜已不在黑暗。
后来,我俩成了闺蜜。再后来,上初中,她家里决定带她去南方的一个城市去读。送别的那天,她把她最喜欢的几枚枫叶送给了我做书签。她说只有枫叶做的书签夹在书中才会越久月香。
在很多个傍晚,我都喜欢站在地平线上,看黄昏把影子拉长,看夕阳把街道染成暖色调。只是,当晚风吹来时,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过期的故事。
突然很想找回那种昔日的感觉。打开一本书,一片叶子从一本书中滑落在地上,我回过神来,在恍惚之间,我看见了一片鲜红的叶子上写了一句话,“这不期而遇的温暖,是谁错过的年华?”
友情,是生命里最长情的守望。相隔千里的闺蜜,请一定要快乐着,如同我们曾经那样的快乐般。做彼此永远的知心,在心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芬芳了我的岁月作文【三】
李欧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读大学,第一次捧读《铁屋中的呐喊》时的震动和愉悦,及至读到他的《狐狸洞呓语》,始在语言的轻松机智和见解的独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欧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学方式和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学术之外的亲切。我耳闻后忙找来一睹为快,同时也在关注网上报端的书评;其间有两则评论、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常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两大问题,剖辨清楚,许多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类问题在于往往把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导致谬误,他再紧抓不放加以发挥,结果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无暇指出文中无数的逻辑漏洞,仅举两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认为“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去打擂,起点就不高”,舒平先生则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一个人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儿培养成才难道没有资格将自己的与众人分享吗?”前者提出的问题是欧梵先生作为在海外多年的学者、知识分子在书写个人记忆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这种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论者认为李先生不应以一个畅销书作家——哈佛女孩的妈妈作为参照(至于到底应不应该,下面会详细讨论),后者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作出回应或驳难,而是粗暴地给对方首先扣上“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然后是近似胡搅蛮缠的发挥,回头一看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前文中讲哈佛女孩的妈妈不能写书了呢?
另有一处,徐慈威举“罄竹难书”一例称《我的哈佛岁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滥造。至少在大陆一般的用法中,欧梵先生确实把这个词一连两次用错了。应该说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单纯的遣字用词,到了舒平的笔下,却颇为高调地称“我辈喜爱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欢李先生那种随意、潇洒,挥洒自然,天马行空的文风”,由“文字”到“文风”,舒先生偷换的概念可谓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认为李欧梵水平粗制滥造(看官注意,这里‘文字’又被置换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仅从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称‘一流’,至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没能被说服!”云云,且不说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时变作了论理的水平,也不说徐慈威先生论理的水平到底怎样,批评对象和批评者之间有无可比,需不需要比,这大概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请舒平先生恕我言语稍有不逊,因为这里实在有些离谱了,“商榷”到最后却质问起批评者的水平以壮声势,实在有些不妥;我其实想说明的还是,当一个概念反复被置换时,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舒文的第二大类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在于舒平本人对于价值的评判缺少一种内在的尺度,这才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和整个文章的“格调不高”。舒文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著述:回忆录、畅销书和学术著作,对于它们评判显然不能执行同一标准:回忆录有自身的精神维度,畅销书要符合的是市场的准则,学术著作也自有一套学术的规范,当然回忆录也可能是畅销书,但总是要遵循最“本己”的价值尺度。舒平本人意识中这种尺度的缺席造成了文章的混乱和可笑,一方面质问“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假借正义之名批判所谓“所谓的学术著作”;尺度的混乱导致对所提及的诸种著述都缺少应有的尊重(误读也是一种不尊重)还是很表面的问题,我说的“内在”是指一本好的回忆录应是一部优秀的精神传记和心灵自传,而不只是身体和经历的纪录,欧梵先生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研究者,作为“中国公共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实践者,作为海外“芝加哥大学中国思想者部落”的酋长,欧梵先生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值得、也引起了无数的关注,人们有理由对欧梵先生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提出更高的期待。舒平试图否定这种期待不仅没有抬高反而降低了这本书应有的品格。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以西方精神为背景、在俄罗斯思想烛照下的真正的“狐狸”,而不是一个在多元文化中栖身或逃避的供人玩赏的画了大花脸的波斯猫——难怪舒平先生那么津津乐道。
最后还是回到欧梵先生的这本新书。为写这篇文章,我把《我的哈佛岁月》又仔细读了一遍,无论是知识还是情感,在这本随性的小书中都很丰富,我认为其中写得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是几篇回忆老师的文字,如《史华慈教授》、《普实克》,《退休记事》也颇为感人,然而毕竟《我的哈佛岁月》是本匆促写成的书,没有来得及耐心地打磨,里面确实存在正如徐慈威先生所指出的一些不妥之处;至于书中“每每津津乐道的男女情爱之事”,徐慈威认为“未免不够恰当”(作为知识性的回忆录),舒平则认为是“率真”,是“真性情”的流露(作为个人的自传),我不作判断,而更愿意把它看作“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不过舒文中说“今年终于读到了一本真正值得一读的书”,我还是觉得有些夸张了,如果舒先生真得这么以为,那实在是井中之论;而在其文末还有一段近似挑衅的话,我看后触目惊心,真真无言以对,其实舒先生多看几遍《我的哈佛岁月》中所论的书与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东汉马援在《戒兄子严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深以为是,并同样以此为戒,愿与舒平先生共勉: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重之爱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饱学之士大多周慎守礼,肤浅之辈大多腾嚣猖狂。这里我绝无嘲讽舒平先生的这篇文章“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意思,我只是私下里觉得徐慈威先生一番寓褒于“贬”的平和之论可能恰恰是对欧梵先生的理解和尊重,不由让人想起书中写普实克教授和夏志清教授笔战的一段,一对朋友间的“笔墨官司”不但没有损害友情,反而见出了双方的学术风度和风范;而舒平先生以剑拔弩张姿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徐文的原意,自说自话近乎无理,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与欧梵先生书中所透露的宽容平和亲切的人文气息相背离,同时也冲淡了回忆所弥散出来的可贵的温情。
芬芳了我的岁月作文【四】
芬芳了我的岁月作文【五】
翻动网页又是一张惊心动魄的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
海平面上升了,海水也发怒了,无情地击打着房屋,激起了几十米巨大的浪花。在我的印象中大海应该是"哗!哗!"地拍打着礁石,溅起几尺高的洁白晶莹的水花。海浪涌到岸边,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海水就像一只愤怒的野兽,让马尔代夫诸多岛国面临着海面上升带来的灭顶之灾,也许几十年之后这里将完全被海水淹没。
点击网页,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原来的北京,可以算得上市一个水乡泽国,老北京有一句谚语“北京城是从河上漂来的”。然而现如今,当时的情景已经难以想象。如今的北京需要从长江引水来缓解缺水之危,北京已连续九年干旱,20xx年更是创造了110天无降水的历史记录……在全世界的首都当中,北京的水资源总量已列在100位之后。城市扩张,人口膨胀,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北京的缺水程度日益加深,而全球变暖更是加快了这一过程的发展速度。可是现在本来肥沃的土地都龟裂了,无一点绿色,本来绿叶丛生的大树都成了这天气的祭品,这荒芜一片的地人迹稀罕,我认为不久以后的今天,会有更多的地方将成为此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图片来提醒人。我多么想去倡议大家环保,我多么想我要用法律为武器,对那些破坏环境的人大声地说:“为了人类的健康,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可爱的孩子,重视污染的严峻形势,还我们一个绿色家园!”
我每当吃完手中的零食,无论走多少路,必定会让垃圾桶把他消化,不会让它高兴太久,从来不会让它随意放肆,每年的5月12日我都会为地球种一棵树,为世界做出一分力,可是这个大道理谁会不懂呢?但又有多少人去行动了呢?
为了我们的生活的家园,让我们少开私家车,少吃异季节的水果,少开空调,等等、等等。也为了我们后代`的有利条件更好,请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后代,保护我们美好的未来。
芬芳了我的岁月作文【六】
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
学者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这话的确精当,与李欧梵自承为“狐狸型”学者可谓款曲暗通,遥相呼应。在治学上,李欧梵多方出击,频频得胜。李欧梵的著作更是纷繁芜杂,极尽“狐狸”之所能。
他的老本行现代文学研究自不必说,一本《铁屋里的呐喊》就把鲁迅打回“人形”。在文化研究上面,一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集现代都市文学、报纸期刊等诸多文化要素研究于一体,奠定其内地文化研究先锋的地位——虽然有人说毛尖女士译得不好,并挑出毛病不下五十处。但至少在我当年读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茅塞顿开。特别是将《子夜》里的小资成分“揭发”出来,以及把张爱玲定位为现代文学史上都市文学的终结者,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此外,李欧梵当年赴美求学时多有寂寞,便以看电影、听音乐打发时间,由此竟也闯出一条新路,从而对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通俗电影有独树一帜的研究。还有,他对上至琼瑶下至王文华等通俗小说也有高见。甚至于日本动漫《风之谷》,他竟用来作为教授卡夫卡的“道具”。可谓大俗大雅,雅俗共赏。凡此种种,可以参见他的新著《清水湾畔的臆语》。
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手术刀”(当然不止于这一把,“狐狸型”学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理论之“刀”又多又快),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老本,文化研究是他的“新欢”,通俗文化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有转为“正业”的趋势)。对此,俨然已是老“狐狸”的他,当然深自明了。
所以,如果对李欧梵这大半辈子作反思,径直可以参见《我的哈佛岁月》“结语”一节。我对此节几乎全部赞同,除了有人说他是“二流学者”,而他却变本加厉地自嘲为“二流学者、三流作家”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之外。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前半句,不同意后半句。就目前来看,如果将李欧梵与他的业师们比起来,“二流学者”他是当定了(这就是吃了“狐狸”的亏)。然而,就写作水准来说,李欧梵不遑多让,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流作家,包括他的情书在内。